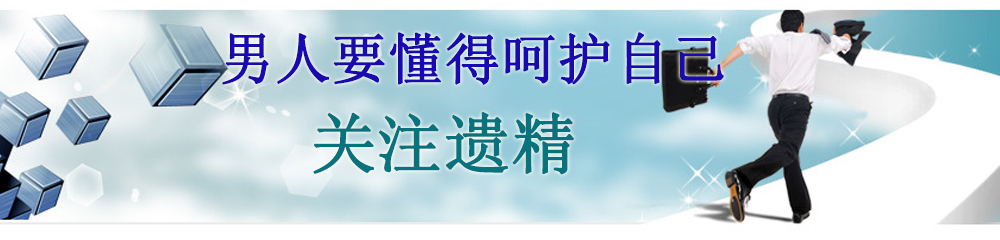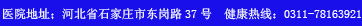蒋勋说红楼梦
2017-9-6 来源:不详 浏览次数:次一
二
三
《蒋勋说红楼梦》节选
任何一个文学或者戏剧,一定是很丰富的,不会仅用一条主线单一地写下去,因为如果只有一条线索的话就不能编织,要有好几条线同时进行,编织才会成功。可是这种编织很困难,在文学、戏剧的创作中,最难拿捏的是在什么时候让这一条线索再适当地出现,或者在什么时候再让这一条线索又适当地隐藏。如果你多读几遍,就会感受到《红楼梦》最精彩的是它的结构,即线索的交错。它在十一回和十二回中基本上略写秦可卿的病,秦可卿的病只变成一个背景,而以贾敬的生日和贾瑞调戏王熙凤这两段故事作为主线,然后到第十三回的时候才跳回来,写秦可卿死了。这就好像我们家里有一个大事要发生,可是在大事发生的同时,其他事情也在发生,这么大一个家族,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发生着。
《红楼梦》的层次很丰富,它就像一棵树,有主干,也有旁枝。它的旁枝非常多,构成了这一棵大树的枝繁叶茂,非常丰富。
贾瑞这个人物,我在第一次、第二次,甚至第三次读《红楼梦》时,都觉得他是最讨厌的一个人,觉得他好下流。但是在最近几次读《红楼梦》时,看到贾瑞这一节,我才忽然感觉贾瑞其实很让人感动。贾瑞本来是一个非常不堪的人。大家肯定记得在第九回,学生大闹学堂,他作为助教,管不住学生,自己还有私心。他的父母双亡,是很严厉的祖父把他养大的,每天叫他跪着背书。可忽然有一天他的情欲一发不可收拾,爱上了一个绝对不应该爱的人——王熙凤。一方面,王熙凤是他的嫂嫂,另一方面,他们的家世完全不般配,而王熙凤又十分厉害。王熙凤每一次故意戏弄他,他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,你会觉得贾瑞是一个笨蛋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,贾瑞其实又体现了我谈《红楼梦》时最常用的一个字——“痴”。他其实很痴,他被王熙凤骗了一个晚上,寒冬腊月蹲在地上冻了一夜,回去又被他祖父打了一顿。第二天他去找王熙凤的时候,王熙凤立刻抱怨他,说你昨晚怎么没有来,他马上觉得是自己错了,赶快跟王熙凤再约。在这种过程中他自己把自己整死了。王熙凤当然厉害,她在利用别人对她的喜欢来玩弄人,每次都给他一个机会,给他一点希望,也给他一点幻想,把对方玩得神魂颠倒,以至肝脑涂地,这就是王熙凤。
其实,贾瑞这个呆瓜被骗的过程是作者刻意要表现的。曹雪芹有一种悲悯之心,他让我们想到贾瑞这种傻傻的、完全没有能力去恋爱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也不少。到最后贾瑞躺在病床上的时候,来了一个跛足道士要度化他,给他一面“风月宝鉴”镜子,说这面镜子是警幻仙姑所制,告诉你一切情欲都是假的,让他不可以看正面,只可以看反面。这里的正与反,其实是在讲情欲的本质有正面与反面,它的反面是一个骷髅,告诉你生命到最后也不过是死亡。可是贾瑞觉得骷髅不好看,这就体现了人性中共同的东西: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死亡。他翻过镜子的正面一看,王熙凤在里面向他招手,他便“荡悠悠”进镜子里跟她做爱,一次又一次,最后“纵欲”而死。实际上贾瑞是被欲望的魔力招走了魂魄。
戏剧在旧时人们的生活中担当着很重要的教化作用,像王熙凤没有读过书,她大部分的历史文化知识都来自戏台。
尤氏的话里提到了季节,说秦可卿陪贾母是在中秋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个很精彩的东西,就是时间或者季节。林黛玉进贾府是正月过年的时候,现在春天过了,夏天过了,中秋也过了,深秋时节,满园的菊花盛开,不知不觉中季节在变。可作者从来不直接讲,但是读者能看到时间的流逝。
秦可卿跟王熙凤本来不是同辈,可是两个人的感情特别好,因为年龄很接近,又都是做媳妇的,而且都在当家。王熙凤在荣国府管上上下下三百口人,秦可卿在宁国府管上上下下三百口人,她们在一起会有很多共同感受。比如她们都容易遭人抱怨,王熙凤狠心、厉害,被人背后骂得要死;可是秦可卿能做到连底下的人都说她好,所以秦可卿内心的委屈比王熙凤多。她们在一起会说起很多理家的辛酸。王熙凤的父亲是九省统制,她是从豪门嫁进豪门,从不忍受秦可卿那样的委屈。但王熙凤特别疼秦可卿,她知道秦可卿做媳妇的难处,从王熙凤的话里可以看出,秦可卿实际上是自己把自己给累死的。
王熙凤跟秦可卿对话的时候感觉很亲,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同病相怜。两个人都是晚辈媳妇管家,管家的难处也只有她们两个人可以懂。管家要得罪人,发现有一个佣人贪污,怎么办?王熙凤是绝对要惩罚的,她是大户人家出来的,比较有经验,处事也利落;可是秦可卿这个女强人做得就非常勉强,背后又没有靠山,怕得罪人,很可能还要帮这个佣人去遮掩,她得把上上下下都打点好,所以特别难。
“凤姐儿听了,眼圈儿红了半天。”注意,王熙凤是一个不轻易感伤的人,她出场时永远是阳光灿烂、欢声笑语的,可是此刻,凤姐眼圈红了半日,这里有某种自怜的成分,她从对方的悲哀里看到了自己的悲哀,王熙凤也有自己的难处。然后,王熙凤半日方说道:“真是‘天有不测的风云,人有旦夕的祸福’。”王熙凤不太容易安静,喜欢风风火火,用“半日”这个词形容她的时候,其实是表明王熙凤状态异常。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”也不太像王熙凤的语言,王熙凤一开口常常不是命令就是骂人,眼下忽然从她的嘴里蹦出来一句诗,说明王熙凤这个时候有了心事,所以这部分不完全在写秦可卿,也是在借秦可卿讲王熙凤内心的一种感伤,她忽然意识到人生的无常。
整部《红楼梦》都在讲无常,贾宝玉是最容易感觉到无常的,他在宴会上常常会忽然哭起来,意识到繁华过去以后的幻灭。而王熙凤很少有这种感觉,她永远觉得眼前的繁华就是繁华,可是在这一刹那间,她忽然有一种无常之感,这不是王熙凤的个性,这时的她显得有些深沉。
贾敬的生日、秦可卿的病、贾瑞爱上王熙凤三条线一直互相穿插着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这种穿插特别精彩,能同时照顾到很多面。十一回里用生日的喜庆去衬托秦可卿的孤单:这边过生日热闹繁华,那边一个病人躺在床上,有很多心事上的纠结。读者会看到人生竟如此丰富,有悲也有喜,有爱也有恨,并不只是一种单向的发展。
《红楼梦》里面每一回都在写人生,让你看到生命的两面:热闹与凄凉,这才是真正的人生。王熙凤要去看秦可卿,有个人一定要跟了去,那就是宝玉。宝玉去看秦可卿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五回中,宝玉第一次性幻想,就发生在秦可卿的卧房。当他第二次走进这个卧房时,卧房的主人将要离世了,这又是一个对比。第十一回呼应第五回:第五回的时候,这个卧房的主人尚处于生命的全盛时期;第十一回里,她已经危在旦夕了。《红楼梦》一直在让你看人生。宝玉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,他忽然觉得人生竟如此虚幻,他曾经在这里梦到的那个美丽世界真似春梦随云散了。
可这个时候你看宝玉在干什么?他根本没有听进去,一直在看墙上的画《海棠春睡图》,看到“嫩寒锁梦因春冷,芳气袭人是酒香”的对联,想到自己以前在这里午睡时做的太虚幻境的梦,然后就开始发呆。宝玉永远能看到人生的两面,这个卧房是他第一次领悟“性”这个奇妙事物的地方,而今天,曾经的繁华春梦不再,一个美丽的生命正在被死神渐渐地夺去光彩。《红楼梦》非常善于用同一个场景让读者看到繁华和幻灭。宝玉“正自出神,听了秦氏说了这些话,如万箭攒心,那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下来了”。
《红楼梦》时间处理得非常精彩,通过这个时间让人感觉到王熙凤此时用情很深,也很真切。王熙凤平常是不太容易表现出深情,可她是真的疼秦可卿,她其实也很喜欢看戏,不过此时她宁愿在病房里陪着秦可卿。
秦可卿也是个聪明人,对自己的病情很清楚,她知道自己的病因是性格所致。一个出身寒门的女孩子嫁入豪门,她承受了太多的压抑、委屈,其实是把自己累死了。
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很有趣,作者用“但见”引出来的。这个“但见”是王熙凤看见呢,还是读者看见,作者并没有明讲,只是让读者觉得,王熙凤走进花园就见到这样的景象:“黄花满地,绿柳横坡。小桥通若耶之溪,曲径接天台之路。石中清流激湍,篱落飘香;树头红叶翩翻,疏林如画。西风乍紧,初罢莺啼;暖日当暄,又添蛩语。遥望东南,建几处依山之榭;纵观西北,结数间临水之轩。笙簧盈耳,别有幽情;罗绮穿林,倍添韵致。”这段文字是什么意思?王熙凤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,但因为这一次是刚刚离开秦可卿的病房,内心所有的哀伤还在,眼前的风景跟她平常看到的风景不一样。她平常看到的风景都是姹紫嫣红的热闹,现在她看到的是满目凄凉,这是在讲她的心情。她走得非常慢,她看到了河流,看到了山脉,看到了小桥,这些句子都在暗示王熙凤内心的节奏在慢下来。她刚刚离开了一个病人,要去看一场很热闹的戏,可是一下子很难转过来,生病的孤独和看戏的热闹中间需要一个节奏的调整。如果她马上就过去看戏,然后开始在那边讲笑话,读者会觉得有点奇怪,这是一个场景与心情的转换。
一般的朋友读《红楼梦》时不太容易理解,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读《红楼梦》,这种地方就跳过了。其实这些是在讲人物的心情,有点像电影里的空镜头。
王熙凤看到满地都是黄色的菊花,看到小山坡上有绿色的柳树,然后有小桥通若耶之溪。“若耶溪”(今名平水江)是绍兴城外的一条河流,传说中西施浣纱的地方。王熙凤走过那座桥,看到流水,她的心情跟很多古典的东西有关联。然后走到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,“曲径接天台之路”。“天台”是在讲汉朝时候阮肇与刘晨进山采药,碰到了仙女,后来被仙女留在山上住了下来。“若耶溪”、“天台山”都是在形容仙境,这么美的风景,是属于仙人的风景。然后她又看水在石头上跳跃碰撞,竹篱上的花掉了下来,满地香味;秋末时节,树叶都变红了,有些已经掉落,已经没有叶子的树林像一幅画一样;秋风越吹越紧,春天已经有点远了,春天鸣叫的黄莺不再唱了,秋天的蟋蟀叫起来了。王熙凤在心情落寞时看到了花,看到了小路,看到了流水,看到了红叶,听到了虫鸣。这些王熙凤平常感觉不到的东西,在这一刻她全部感觉到了。作者在此处加入的这一段文字非常重要,它是王熙凤心情的写照。就像《牡丹亭》里的杜丽娘游园,游的是自己心事的花园,是她自己荒凉感伤的内心的衬托。很多学西方文学评论家说《红楼梦》没有心理描写,其实《红楼梦》的很多心理描写是借诗文在传达的。作者常常很刻意地跳出故事的叙述,忽然写出一段诗文,此刻人物的心情就被描绘出来了。请大家特别注意,《红楼梦》里凡有诗词歌赋出现的时候,都是在描写心情。
秦可卿在走向死亡,贾瑞也在走向死亡。其实十一回、十二回这两个人是写在一起的。秦可卿优雅、美丽、高贵,贾瑞下流、低级、卑微,但是两个人都是因情而死。还记得警幻仙姑跟贾宝玉讲过“情既相逢必主淫”,作者一直相信情与淫是分不开的,我们既然看到秦可卿“情”的部分,也要能看到贾瑞“淫”的部分。作者认为情与淫根本是同一件事,“情”是精神已经升华到干净高贵的境地,“淫”是肉体上没有办法克制的欲望。
现代人能够对情欲有所同情,可在古代是不可能的。现代人会为潘金莲讲话,可是古代人就认为她是淫妇。她的结局就是要让武松挖出心脏来祭武大郎。《红楼梦》里借贾瑞讲情欲,对情欲有一定的悲悯,其实就是一种包容。在作者眼里,情欲有不可抑制的悲惨在其中。秦可卿的死和贾瑞的死,共同特点就是“情”没办法有完整的寄托。如果回到原来的版本,秦可卿是因为公公爱她,逼奸而死,淫丧天香楼,也是个“淫”字,就更能明白贾瑞之死跟秦可卿之死,从十一回、十二回到十三回其实是在讲同一件事情。
凤姐真是坏,她是聪明人,聪明人的坏是最不可原谅的,此时她完全在利用贾瑞的痴情,她一生眼里从不揉沙子。她后来的下场很惨,这是一种人性上的因果。
“说话之间,已来到了天香楼的后门。”“天香楼”这几个字出来,你会吓一跳,因为《红楼梦》现在留下的另一个版本就是“淫丧天香楼”。如果没有改的话,大家就能明显看到贾瑞的“淫”与秦可卿的“淫丧天香楼”是同一类事件,都是情欲不可自制的乱伦,结局都是死亡。如果小说不作修改的话,这种感觉会比较强烈。
“凤姐儿听了,款步提衣上了楼来。”《红楼梦》里面的女性是穿旗装的,脚下是高跟的鞋子,那个跟儿不是放在鞋后面,而是放在鞋的中间,所以她上楼的时候,一定得提起衣服,然后上楼。这从侧面证明当时的贾家是旗人贵族,也就是满清贵族,穿的是旗装。
戏曲在《红楼梦》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,点戏能反映出人物的个性,比如林黛玉和薛宝钗点的戏永远不一样。
王熙凤看了戏单,点了《还魂》、《弹词》。王熙凤平常绝不会点这种戏,因为《还魂》、《弹词》都是很哀伤的戏。《还魂》讲的是杜丽娘梦到跟柳梦梅前世姻缘未了,云雨一番,醒来后怅然若失,说这个人如果不在人间,我宁可死去,跟他再相会。于是杜丽娘从此不吃不睡,最后便病死了。病死之前她画了一张自己的画像,卷起来丢在花园里,说是不管来世或者今生,只要这个男的来到这个花园,还会找到她。几世几劫后,柳梦梅真的来了,他捡到了这张画,就把画挂起来,他惊诧世间竟有这么美的女子,就不断地说:“你出来。”最后杜丽娘真的借这张画“还魂”了。
《弹词》是《长生殿》结尾部分的一折,一个在繁华盛世时曾为唐玄宗演奏的音乐家李龟年,年老时流落江南,行乞街头,他用一个弦子弹拨,唱起了当年的繁华故事,叫做《弹词》。这两个戏都是对繁华的回忆,都是哀伤的戏。这里仿佛是在呼应秦可卿之死,或者贾瑞之死也在里面,让人感觉到这些人热闹的时候,还有两个人以不同的形式走向死亡。王熙凤鬼使神差地就点了《还魂》和《弹词》。这里凤姐点的戏其实是在呼应后面的情节,预示着繁华背后的凄凉。
《红楼梦》里有非常丰富的不同人物的个性,随着时间的流逝,三百年过去了,大家仍然会觉得里面的人物活在现代。像贾瑞这样的角色,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常见,他们陷溺于不可自制的情欲世界,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。
小说写秦可卿的死,告诉你情都是空幻的;写贾瑞的死,告诉你肉体上的沉溺也是空幻的,情与淫在这里合写。
人世间每一个的生命,都自有其贵贱贫富,可在曹雪芹的眼中,已经毫无差别了。每个人在受他自己的命运的苦。不同命运的苦,都是不自知的,同贾瑞的不自知一样,王熙凤也不自知。
如果这一段没有写“风月宝鉴”,只写贾瑞死在床上了,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领悟。作者其实是在借贾瑞告诉我们,《红楼梦》里面大大小小的人物,都在不同的情欲里纠缠,是他们自己一直以假为真,导致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。第五回贾宝玉看到的太虚幻境里面就是这一句话。加上“风月宝鉴”这一段,说明贾瑞这个角色是作者刻意要写的,他要告诉我们人性里最难堪的一面,而这最难堪的一面是任何人都可能会经历的。
西方的美术史里面常常有骷髅,修行的时候旁边也有骷髅头,是要告诉你生命的终结就是这个,你每天看,就能提醒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假的。作者要借风月宝鉴度化贾瑞,告诉他你最后就是这个样子,现在有什么好邪思妄动的,你所拥有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幻象。
他已经忘了道士跟他说的话,因为反面不好看,他就翻过来,看看正面是什么,“想着,又将正面一照,只见凤姐站在里面,招手叫他”。他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幻象。所以,有没有镜子不重要了,是他没有办法忘掉凤姐,王熙凤变成了他的致命伤。“贾瑞心中一喜,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,与凤姐云雨一番。”“荡悠悠”用得极好,其实贾瑞已经快死了,大概是他的精神进去了,跟凤姐发生了性关系。“凤姐仍送出来。到了床上,‘哎哟’一声,一睁眼,镜子从里调过来,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。”这一段完全像神话,可是非常精彩,刚做完爱出来就发现骷髅又在面前,其实就是生死。我们看到人生的两面,繁华与幻灭、情欲的快乐与死亡的空虚在做对比。可是这么生动的提示都没有让贾瑞领悟,他大叫了一声,“自觉汗津津的,底下已遗了一滩精”。
贾瑞后来遗精而死,因为他一直在看镜子的正面,一直幻想跟凤姐做爱,一次又一次地耗尽精血。写情欲之悲伤,大概没有像《红楼梦》写得这么惨的。这个时候你忽然会回想起贾瑞之前讲的“死也要来”。现在他就是一次一次到镜子里面去赴死亡之约,这大概真的是他要还的冤孽之债。
“心中到底不足,又翻过正面来,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,他又进去,如此三四次。”人无奈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,一次不够,两次、三次。他就是不要看那个骷髅,他永远不能面对生命的本质。那个跛足道人其实早已知道,贾瑞必须走,走之前给他照一照镜子,让他明白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
“到了这次,刚要出镜子来,只见两个人走来,拿铁锁把他套住,拉了就走。”在中国古代小说里,拿着铁锁前来的都是阴间的差使,西方常常是一个拿镰刀的死神。“贾瑞道:‘让我拿了镜子再走。’——只说这句,再不能说话了。”他要拿镜子,还是因为凤姐在里面。
“旁边伏侍贾瑞的众人,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,落下来,仍睁开眼拾在手内,末后镜子落下来,便不动了。”贾瑞死了,旁边的人只看到他在照镜子,贾瑞看到的幻象旁人是看不到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幻象与情欲别人都看不到,只有自己知道。
作者写贾瑞的部分写得非常深,我很希望从贾瑞的死亡中,大家能感受到作者深刻的悲悯之心,他特别安排了这个道士,好像要度化他。如果贾瑞没有被度化,读者会被度化吗?我们不敢肯定。即使不能度化,也一定会知道人有共同的悲哀或者无奈,这才是《红楼梦》真正要让人领悟的。很多人简单地认为,《红楼梦》就是让你最终领悟佛道的四大皆空,然后出家,像高鹗补的后四十回里贾宝玉最后出家了,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了。作者对人生有很多经验和积淀,他也知道,就算到庙里也可能心不静,说不定还会把镜子带到庙里面去,所以作者让你觉得,到最后度化都有可能成空。因为如果你在度化里没有领悟的话,你还要一次次承受人生的折磨和煎熬。他讲得非常深刻,让人认识到,修行是要回到人间修,回到生活里修,甚至回到情欲里修的。如果真的是必须回到情欲里修,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贾瑞也是在修行,被情欲所制很可能这就是他修行的方法,他一生就是用这么难堪的方法来度化自己。
“以假为真”,是《红楼梦》里非常深的格言。在人间行走,我们都在不同程度地以假为真,作者对人生最大的领悟与最大的悲悯也在于此。作者没讲明到底什么是真的,真的难道就是那个骷髅吗?那么在成为骷髅之前人的生命到底要怎么度过?如何自处?他也没有讲。这里作者只是提醒,让你觉得你眼下所眷恋、执著、放弃不了的东西,其实都是梦幻泡影。我不认为《红楼梦》是要你放弃对生的所有眷恋,只是在提醒你没必要对终成虚幻的东西过于执著。
文学不是哲学,我不赞成把小说当成一个格言或真理奉行一世。很多人读《红楼梦》一定要说自己领悟了,如何如何。其实,对《红楼梦》的领悟永远在生活的过程当中,就是让你每一时每一刻都有新的感悟。永远是昨天看时觉得应该如此,今天看时又有所修正,今天看时以为真了,第二天看时又有点假。这就是为什么《红楼梦》会吸引你一直读的原因,它让我们觉得生命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。
贾瑞的故事结束了,他是《红楼梦》里最微不足道、最卑微的一个人,可是这一章在小说里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章。作者在收尾的部分又讲到林如海的死亡。
《红楼梦》是一部感伤的书,它让人看到了繁华富贵的短暂和最后的幻灭。
对秦可卿的死真心哀痛的大概只有宝玉,因为她是宝玉最早的性幻想对象,当宝玉知道她死了之后,一口鲜血喷了出来,宝玉对人有一种真情,其他人不过是走过场。
曹雪芹在家败人亡之后写这部小说时,回忆当年的繁华富贵,这其中包括丧礼的风光,他有一点茫然,感觉到人事的空幻,所以在他笔下,死亡这样的事件也好像一场戏一样。
《红楼梦》修改了十年,其中透露出作者从完全率真地要呈现家族历史,到最后用很多神话把真事隐去,借用假语村言,在真和假之间做了调整。现在大家都希望了解《红楼梦》最早的版本和后来修改的刊印版本之间的差距,其实,其中差距最大的就是第十三回“淫丧天香楼”。如果这是最初的版本,恐怕秦可卿的死是这个家族中最令人震惊的大事,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上吊而死,以及上吊的原因。这个时候办这个丧事,即使再风光,也隐藏不住其中惊人的真相。
作者将秦可卿的死改成病死的时候,心里有另外一种痛。所以作者并没有直接去写秦可卿的死亡,而是很奇怪地写到王熙凤,说她睡了以后恍恍惚惚地看到秦可卿进来了。我认为《红楼梦》非常精彩的部分都是从真实入梦、从入梦到真实的过程。第五回也是如此,贾宝玉喝醉了酒,恍恍惚惚觉得秦可卿在跟他讲话,带他到了太虚幻境。他在太虚幻境经历那么多事,忽然醒过来。他由梦入真、由真入梦之间的关系非常自然。
曹雪芹刚开始写《红楼梦》时,是不太在意别人看的。他在人生最后的十年中回忆自己一生的悲哀,很大胆地写这部小说,原本是写给自己看的。可是小说写了一半以后,便陆续有人翻阅了,他忽然意识到有读者,下笔时多多少少会考虑到读者的反应。
我不觉得《红楼梦》是一个让你领悟空幻的小说,即使一秒钟的缘分,如果珍惜,它就是很深的缘分。
因为元春生在大年初一,就叫元春,所以这个家族的女孩子后来都叫春,元春之外还有三个女孩子。贾赦这边生了一个女儿迎春,贾政跟妾赵姨娘生了一个女儿叫探春,宁国府贾珍有一个妹妹叫惜春。把四个女孩子的名字连一起,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,是“元迎探惜”,也就是“原应叹息”这四个字。元春嫁到皇宫,一辈子见不得亲人。迎春是一个二木头,有一点憨憨傻傻,后来嫁给一个外号叫做“中山狼”的男人,每天打她。探春呢,是庶出的,在家族里面地位非常低。在这个家族里面,她的身份一直很特别,她很能干,非常聪明,做人处事都非常好,可是她妈妈永远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她,说你是小姐了,你就看不起你妈妈,后来探春远嫁。惜春的结局是出家做了尼姑。“原应叹息”,大概是作者回想自己几个姐妹的下场,有一点感叹吧。
曹家在被抄家之后,家族落难到惊人的地步。据说,曹雪芹后来在今天北京的香山附近举家靠喝粥度日,穷到连饭都吃不饱。这个在十四五岁以前一直过着富贵荣华生活的公子哥儿,大概从来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落难到这个地步。他没有一技之长,也没有生财之道,结局非常惨。其实秦可卿讲的这些话,正是曹雪芹为家族当年繁华时没有为未来做准备而发的感慨。
《易经》里面有六十四卦,这六十四卦的卦象大部分都有起有落,坤在上,乾在下叫“泰卦”(け),是六十四卦里比较好的卦,大部分都是吉。“否卦”(お)与“泰卦”正好相反,乾在上,坤在下,是六十四卦里比较坏的一卦。《易经》认为可以转动的状况是好的,天在上,地在下是正常的、不会变化的状况,而“否卦”到了极限,就一定会转好。《易经》的思想是认为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情是永远好或永远不好的,而是循环变动的,所以下面就说“荣辱自古周而复始”。荣华富贵跟屈辱败落是周而复始的,是循环的。汉朝的皇宫都叫未央宫,“未央”就是不要到中心、中央。为什么?因为到了中央就要走下坡路了,所以最好保持在一个永远可以往上发展的状态,不要到头。“乐极生悲、否极泰来”,这里的“极”都是指太过了。
曹雪芹在人生最后没有退路的时候,忽然想到当年怎么没有做这件事,因为他后来住在北京香山,据说香山就是曹家原来发迹的地方。如果当初这个地方还有田产、房屋的话,他就不会惨到连日子都过不下去。
我们来看曹雪芹的家族,曹寅是和康熙皇帝一起读书长大的,因为他的妈妈是康熙的奶妈。康熙做了皇帝,江南有一个肥缺,当然要找和他一起长大的亲信去做,就让曹家去做了巡盐御史。这个巡盐御史表面是一个肥缺,可是私下更重要的,还兼具皇帝眼线的角色,所以一定要是皇帝的亲信。康熙在位时间很长,所以曹家可以受到上百年恩宠。曹寅过世前,康熙皇帝亲自派御医快马加鞭地送药到他家,可见曹家当时受宠幸的程度。从曹寅一代到曹雪芹一代,三四代下来,雍正五年时曹家被抄家,因为雍正要启用自己的亲信,老爸的奶妈不见得和他有那么亲,曹家在政治斗争当中被弃用了。
《红楼梦》对于人事关系、对于人世间的权势了解得太透彻了。这份透彻来自这个家族繁华过又败落过,只见过繁华,没见过败落,就不会如此透彻。曹雪芹在这里借秦可卿之口讲出家族的难题,有一部分可以跟作者的个人经验结合。
最大的悲哀还是说秦可卿这个寒门女子,生是贾家的人,死是贾家的鬼,临死了还要呕心沥血地为贾家着想,考虑退路。如果真的有这个角色的话,作者对她是抱有最大歉意的,因为秦可卿嫁到这个家族后受到的委屈最深、最难以言说。如果她是被公公逼奸而死的话,那她死后那个风光的丧礼,就变成了巨大的嘲讽。
秦可卿在第十三回就死了,可是一直到八十回,她还无时无刻不在出现。每次贾家有什么事发生,就会听到有人在叹气,那就是秦可卿。秦可卿是一个死而不去的幽魂,她成了贾家最大的一个感伤。从秦可卿死的这一段可以感觉到,秦可卿的死不只是一个肉体的死亡,她还变成了一缕幽魂,幻化在贾家,其实秦可卿本身就在警幻,告诉你一切都是假的,都是幻象,必须及早领悟。
医生给秦可卿把脉时曾说,她这个病不是药可以医的,因为她心性太强,做人总想要做到完美,什么人都不得罪。从这几句话里,可以看出她做人真是做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,她活得也太小心了。虽然秦可卿是十二金钗里面第一个死的,可也是十二金钗里最完美的,好像没有一点缺陷。然而她没有缺陷是因为她一直在人前努力撑着,让人家觉得她是完美的,连最后死亡的时候还要托梦,把这个家族以后的事情做个交代。
《红楼梦》绝对不是一本不食人间烟火只谈儿女私情的书,而是一部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深入记述的百科全书。很多人喜欢读《红楼梦》是因为林黛玉和贾宝玉,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,他们两个已经很久没露面了。《红楼梦》根本不只是写他们,只是借着这一对小儿女的情爱,带出了人世间复杂的生活层次和社会层次。
我一直有个很大的愿望,希望现代人能够从现代的角度去诠释《红楼梦》。一部好的、伟大的文学作品,如果只在古代是伟大的,对现代人没有意义,就没有传世的必要。今天读《红楼梦》,你仍然可以从中学到管理学的知识,对于人的教养有所思考,对政治有所反省与觉悟,这才是《红楼梦》更有价值的部分。
赞赏